高考作文素材篇:偶然与命运!范赏和导读!
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偶然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一种不可控制的规则,必然则是根据的发展联系所不可避免的结果。人都是想要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可以在一切坏的事情到来之前做好一切的防御措施,但是生命的精彩之处不就是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吗。偶然与命运看似不可相连,但是却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这个命题的意义大概也就是如此吧!命运一偶然而产生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偶然与命运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年轻的时候喜欢写剧本。他写了一部诗剧《忒耳西忒斯》,引起了普鲁士剧院的兴趣。剧院老板写信给他,表示要在柏林的皇家剧院首演这出剧,并请当时较的演员马特考夫斯基出演阿喀琉斯这个角色。茨威格说他当时“简直惊喜得目瞪口呆”。但是,就在茨威格订好了前往柏林的车票准备看演出时,接到了一封电报——马特考夫斯基患病,演出延期。几天后,报纸上就登出马特考夫斯基逝世的消息。茨威格没有想到,这个意外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来,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接踵而至。他不再是“惊喜得目瞪口呆”,而是惊呆了。
不久,另一个被茨威格“奉若神明”的伟大演员凯恩茨,要求出演《忒耳西忒斯》剧中忒耳西忒斯一角,并请求茨威格再给他写一个独幕剧,以供他客串之用。三周之后,茨威格将初稿交给凯恩茨,得到凯恩茨的高度赞赏。凯恩茨反复吟诵之后感觉已“十分”,二人约定一个月后,在凯恩茨演出归来后正式排练这部短剧。然而,茨威格等到的却是病入膏肓的凯恩茨。几周后,凯恩茨就病逝了。
这两个意外纯属偶发事件,却足以让茨威格感到恐惧。以后凡是演员出演他的剧本,他一概拒绝。但是,凶煞之神关闭了一扇门,却从另一扇溜了进来。这次是一位导演,他刚根据茨威格的剧本完成导演手本,还未来得及开始排练,过了14天就死了。十几年后,茨威格写了一个剧本《穷人的羔羊》,他的朋友、演员莫伊西要求担纲主演,被茨威格坚决拒绝——他心里存在的巨大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又过了若干年,莫伊西要演出意大利作家皮兰德娄的《修女高唱五月之歌》,首演将在说德语的维也纳举行,皮兰德娄委托莫伊西请茨威格翻译成德语。茨威格觉得这次只是翻译,不会有什么事情,同时也为了给皮兰德娄和莫伊西两个朋友面子,就完成了这项工作。没有想到的是,仅排练了一次,莫伊西就患了重感冒,接着高烧不退,神志昏迷,两天之后,就驾鹤西去了。
茨威格是小说家、剧作家,但这段经历既不是小说,也不是剧本,而是现实中真实发生的。这其中充满巧合、偶然、命运等戏剧性因素,但它不是戏,是人生的本来面目。而较大的悲剧发生在茨威格自己身上,这部《昨日的世界》是他流亡巴西时写的,1940年左右写毕,但两年后书还未出版,他就以自杀的方式告别了这个“昨日的世界”。
偶然是命运无常的较大注脚,或喜或悲,或好或坏,常常有偶然这只无形的手在导演。茨威格所经历的,我们无法找出其中必然的存在。面对这些不可知的偶然事件,泰然自若、顺应接受是较好的办法,怨天尤人、自叹命苦都于事无补。#p#分页标题#e#
当然,茨威格并未把偶然事件和命运等同起来,他说:“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原来是由内在因素决定的。看来,我们的道路常常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莫名其妙和没有道理,但它较终还是会把我们引向我們自己看不见的目标。”这是智者的清醒之语。
【外一篇】
安静的时光
威尔·施瓦尔贝
托比·坎贝尔是一名肿瘤,在临终医院和临终关怀机构工作。
在威斯康星州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他正在探访一位名叫吉斯的病人。吉斯被认定只能再活几天,于是医院就让他出院回家度过较后的日子。但是吉斯又顽强地活了三个月,吉斯的家人和朋友围在他身边,为他依然活着庆祝了一次。
后来,吉斯还活着,他们又庆祝了一次;之后,他们庆祝了第三次。吉斯的生命的確在流逝——这一点毋庸置疑——只是不像大家预想的那么快而已。
他向坎贝尔医生吐露心声,说他现在感到筋疲力尽,这并非因为疾病,而是他身边人都试图让他生命中仅存的每一刻都过得有意义,因此,他没有一点属于个人的时间。
坎贝尔医生意识到,尽管他曾经治疗过几百名濒临死亡的人,但是他关于生命尽头的理解可能被误导了——持续的高强度生活会让人感到疲惫不堪。
其实,吉斯并没有需要去实现的遗愿清单。他热切地希望能够无所事事地度过一段时光:也许是小睡一会儿,也许是随便看看电视节目,并且不为此产生罪恶感或遗憾。
其实,每整天,我们都需要一点儿安静的时光,来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漫长的一生更需要这样的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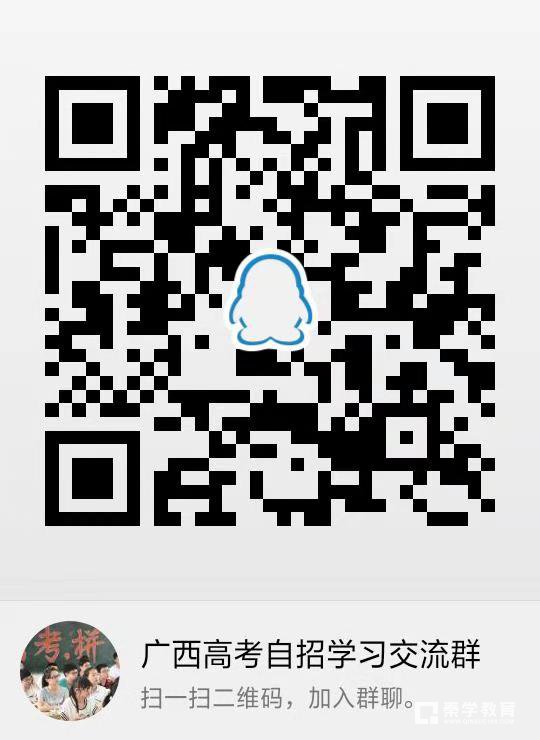
- 热门课程
- 热门资讯
- 热门资料
- 热门福利
-
 渭南艺考生集训班推荐哪个?学大提分快吗?渭南有很多艺考生文化补习机构,家长们想给孩子挑选口碑好,补习效果好的,真的是看花了眼呢!有的家长说自己一天转了5家机构看来看去也觉得差不多,有的是管理严,有的是中考做的好,想找到真正适合孩子的补习机构还是要看能不能对其颗粒度。本期咱们就来聊聊学大教育吧!
渭南艺考生集训班推荐哪个?学大提分快吗?渭南有很多艺考生文化补习机构,家长们想给孩子挑选口碑好,补习效果好的,真的是看花了眼呢!有的家长说自己一天转了5家机构看来看去也觉得差不多,有的是管理严,有的是中考做的好,想找到真正适合孩子的补习机构还是要看能不能对其颗粒度。本期咱们就来聊聊学大教育吧! -
 荨麻的“荨”怎么读?“荨”字什么意思?宝子们,荨麻这个词大家肯定在日常生活中见过,那这个“荨”字怎么读呢?它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大家对这个字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下文的内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荨”怎么读? “荨”是多音字,指代“荨麻”时读qián,用于“荨麻疹”时读xún,另有古音tán(通“燂”或指知母),现较少用。 其核
荨麻的“荨”怎么读?“荨”字什么意思?宝子们,荨麻这个词大家肯定在日常生活中见过,那这个“荨”字怎么读呢?它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大家对这个字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下文的内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荨”怎么读? “荨”是多音字,指代“荨麻”时读qián,用于“荨麻疹”时读xún,另有古音tán(通“燂”或指知母),现较少用。 其核 -
 渭南学生走单招推荐伊顿单招吗?怎么收费?渭南的学生最近有很多都想找个单招补习的机构,3月15也是陕西单招考试的时间了,在一周的时间里很多学生觉得一些技巧和面试的重点细节还没掌握,所以想找个单招冲刺营,那么本期小编就来推荐一下伊顿单招吧!
渭南学生走单招推荐伊顿单招吗?怎么收费?渭南的学生最近有很多都想找个单招补习的机构,3月15也是陕西单招考试的时间了,在一周的时间里很多学生觉得一些技巧和面试的重点细节还没掌握,所以想找个单招冲刺营,那么本期小编就来推荐一下伊顿单招吧! -
 西安秦学伊顿中考冲刺怎么样?初三语文怎么提高?距离中考所剩的复习时间已经不多了,学生们的备考时间比较紧张,很多学生的语文基础不够牢靠,阅读和作文得分不高,复习找不到重点,成绩提升慢,家长也跟着焦虑。就有一部分的西安家长想了解秦学伊顿的中考冲刺效果到底怎么样?能不能帮孩子实实在在的提分,那么,今天小编就给大家来具体分享一下吧! 西安秦学伊顿
西安秦学伊顿中考冲刺怎么样?初三语文怎么提高?距离中考所剩的复习时间已经不多了,学生们的备考时间比较紧张,很多学生的语文基础不够牢靠,阅读和作文得分不高,复习找不到重点,成绩提升慢,家长也跟着焦虑。就有一部分的西安家长想了解秦学伊顿的中考冲刺效果到底怎么样?能不能帮孩子实实在在的提分,那么,今天小编就给大家来具体分享一下吧! 西安秦学伊顿
-
 2022西安高考地理考前冲刺及答题技巧梳理班招生开始各位西安市的学生现在高考距离我们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在这最后两个月大家一定要抓紧。为帮助各位学生在最后阶段冲刺,伊顿教育推出了高考政史地考前冲刺及答题技巧梳理班,帮助大家备考解决考试中的易考点和难点。下面小编老师为大家整理了高考地理考前冲刺班招生电话和地理考试知识点相关内容,大家了解一下! 20
2022西安高考地理考前冲刺及答题技巧梳理班招生开始各位西安市的学生现在高考距离我们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在这最后两个月大家一定要抓紧。为帮助各位学生在最后阶段冲刺,伊顿教育推出了高考政史地考前冲刺及答题技巧梳理班,帮助大家备考解决考试中的易考点和难点。下面小编老师为大家整理了高考地理考前冲刺班招生电话和地理考试知识点相关内容,大家了解一下! 20 -
 2022年高新一中第八次大练习试题及参考答案各位西安市高三的学生现在大家都在经历各种高三的模拟考试吧,高新一中的试题大家想不想要了解?名校试题大部分的学生都想参考,为方便各位学生了解,小编老师为大家整理了2022年高新一中第八次大练习试题及参考答案,想要了解高新一中试题的学生看一下!更多有关西安高三高考模拟测验的相关信息资料欢
2022年高新一中第八次大练习试题及参考答案各位西安市高三的学生现在大家都在经历各种高三的模拟考试吧,高新一中的试题大家想不想要了解?名校试题大部分的学生都想参考,为方便各位学生了解,小编老师为大家整理了2022年高新一中第八次大练习试题及参考答案,想要了解高新一中试题的学生看一下!更多有关西安高三高考模拟测验的相关信息资料欢 -
 2022年咸阳市高考模拟检测试题,咸阳高中辅导班整理!现在2022年高考距离我们还有两个月左右各位高三的学生现在准备好冲刺了吗?现在各位高三学生的模拟考试一定非常多,对于考试大家一定要认真的查漏补缺。为方便各位学生了解,小编老师为大家整理了2022年咸阳市高考模拟检测试题和答案,想要了解的学生看一下!更多有关高考考试资料和相关辅导信息大家
2022年咸阳市高考模拟检测试题,咸阳高中辅导班整理!现在2022年高考距离我们还有两个月左右各位高三的学生现在准备好冲刺了吗?现在各位高三学生的模拟考试一定非常多,对于考试大家一定要认真的查漏补缺。为方便各位学生了解,小编老师为大家整理了2022年咸阳市高考模拟检测试题和答案,想要了解的学生看一下!更多有关高考考试资料和相关辅导信息大家 -
 西安高中辅导班,西安中学高2022届第三次模考文科数学试题分享!各位西安市的学生大家对西安中学了解吗?西安中学也一所重点中学目前第三次模拟考试已经结束,不少的高三学生想要参考西中的考试资料。为方便各位学生了解,小编老师为大家整理了西安中学高2022届第三次模考文科数学试题资料,想要了解的学生看一下!更多有关西安高中全科辅导班的相关信息,各位学生可以拨
西安高中辅导班,西安中学高2022届第三次模考文科数学试题分享!各位西安市的学生大家对西安中学了解吗?西安中学也一所重点中学目前第三次模拟考试已经结束,不少的高三学生想要参考西中的考试资料。为方便各位学生了解,小编老师为大家整理了西安中学高2022届第三次模考文科数学试题资料,想要了解的学生看一下!更多有关西安高中全科辅导班的相关信息,各位学生可以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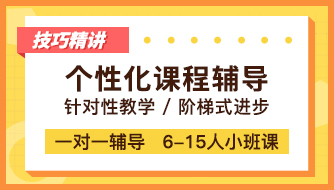








 All right reserved
All right reserved
